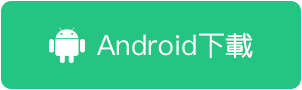這天夜裡,鄢月正睡着,突然感覺有人站在床邊。她心下一驚,伸手就抽出枕邊的短刀。
「別動手,是我。」一低沉的聲音傳來。
鄢月一愣,眯着雙眼仔細看去,原來是之前闖入她房間的那個銀面男人。當即自嘲:這月府的守衛還真成了擺設,任由他來去自如。
「你的警覺性還真高,我這才進來沒多久啊。」
鄢月坐起身:「你來幹什麼?」
「找你聊聊。」銀面男說着,揚了揚剛在書架里找到的那張三皇子畫像,「你怎麼能把人畫得這麼像?跟誰學的?」
「我為何要告訴你?」鄢月挑眉,「你都不以真面目示人,憑什麼來問我這個?」
銀面男呵呵一笑:「現在不是時候,總有一天,我會讓你看的。」
「那你叫什麼,是什麼人?難道這也不是時候讓我知道?」
「聰明。」銀面男打了個響指,將畫像放回書架。鄢月不由得翻了個白眼。
「你這丫頭,會功夫,會碳畫,還會即興歌舞,到底跟誰學的?怎麼以前一點都沒顯露過?」
鄢月斜睨了他一眼:「你不知道有一句話叫『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嗎?」
銀面男低聲笑着:「好吧。那我問你,你真情願嫁給那個傻子?」
鄢月沉下臉:「這關你什麼事?」
「我好奇。以你這麼聰慧的人,怎麼會甘心嫁給一個傻子?」
「誰說傻子就不好了?這世上我若一定要嫁,那就嫁他。至少,我會過得開心。」
「你……認真的?」銀面男眼神複雜的看着鄢月,「若你是迫於皇家嚴威而不得不答應,那我可以帶你走。」
「啊?」鄢月詫異萬分,「帶我走?」
「是啊,這樣你就不必委屈的嫁給那個傻子了。」
鄢月給了他一個冷眼:「張口傻子閉口傻子,傻子怎麼了?我就情願嫁給他,不用你多管閒事!」
「你……」銀面男瞪着鄢月,許久收回目光,輕笑一聲,「好吧,沒事了,我走了。你自己多加小心,似乎……有人在監視你。」
鄢月一愣,轉念之際,人已離開……
翌日,有丫環前來傳話,說月夫人想見見鄢月。
這月夫人一直臥病在床,自鄢月進入月府,都一直未見過,如今聽說是身子好了些。
「小舞,苦了你了。」月夫人半躺在床上,消瘦蠟黃的臉上,帶着一絲疼惜,「本來我和老爺是想讓你做五皇子妃的,可沒想到……」
鄢月心下一暖:「母親,如今這結果,我並無任何不滿,只要日子過得開心就好。」
「唉,苦命的小舞。」月夫人拍了拍鄢月的手,眼眶逐漸濕潤,「你自小就沒了娘,我心疼你,想養在身邊,可終究因為這病,而不能照拂好你。老爺也疼你,本來想給你一個好的歸宿,可現在……」
「我沒關係的,母親,最重要的是你要養好身子。醫仙這段時間不是在府上嗎,讓他多來瞧瞧。」
「我這還有什麼好瞧的,倒是你,我放心不下。」
鄢月笑了笑,正想說些什麼,突然聽到一丫環來傳話,說是抓到了當初害月舞的兇手。鄢月一愣,匆匆辭別了月夫人,趕去大廳。
此時,廳中已然站滿了人,幾位主子都到了。鄢月一眼便見一三十來歲的男人跪在地上,而二姨娘則一臉驚訝。
「爹,就是這個男人嗎?」
「嗯,說起來,這還是二姨娘的遠親呢。」月霄說着,眼神凌厲的看向二姨娘。
二姨娘神色一變,指着那男人道:「老爺,他是我遠親不錯,可、可他傷害四小姐絕對與我無關啊。」
月霄不為所動,冷冷道:「有人見他拿着一個上好的玉鐲去當鋪,途中不小心說漏了嘴,說是因為他替你辦了件事,所以才得了那鐲子。」
「不,我沒有,我沒給過他任何東西!」二姨娘矢口否認。
那男人聽罷,猛然抬起頭:「二姨娘,你這麼能這麼說,明明是你要我辦的事,事後還給了我一個玉鐲,說是獎賞給我的,怎麼能說沒有呢?」
「你……你胡說!」二姨娘氣得渾身發抖,一把揪着那男人的領子,「是誰,是誰要你來陷害我的?」
那男人從懷裡拿出一通體碧綠的鐲子:「這明明是你給我的啊,什麼陷害?」
二姨娘一見那鐲子,頓時瞪大雙眼:「這……怎麼會在你手裡?你什麼時候偷去的?」
「二姨娘,沒想到你有膽吩咐我去做,卻沒膽承認啊?沒事我去偷你鐲子幹嘛?這是你賞給我的啊。」
「不……不是。」二姨娘拼命搖頭。月茹和月晴杵在一旁,不敢支聲。月齊扁扁嘴,噙着眼淚怕怕的縮到了月茹懷裡。
鄢月瞥了眼月畫,見其一臉平靜,全當看戲。
「那當初,是你將我擄走,毀容丟河裡的嗎?」鄢月緊盯着那人,問。
那人點頭,爬到鄢月腳邊不停地給她叩頭:「是,是小的做的,四小姐,是小的一時糊塗,見錢眼開,聽從了二姨娘的吩咐,差點害死你。小的對不起四小姐,還請四小姐看在小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饒了小的死罪吧。」
鄢月定定的望着他,幽幽開口:「既然如此,你且告訴我,當初,你用刀子在我左臉上劃了幾下,在右臉上劃了幾下?」
說完,她不着痕跡的看了眼月畫,卻見她微不可察的皺了皺眉,當即心下冷哼。而秦泰亦是愣了愣。
「這……」那人猶豫着,「當時小的心裡也害怕,實在、實在不記得劃了多少下。對不起,四小姐,小的、小的糊塗,做下這等惡事。」
「那你用刀劃了我額頭嗎?」鄢月繼續問。眾人皆一副不解的神情:事到如今,還問得這麼仔細做什麼?
「這,小的不、不記得了,當時、當時真的害怕,只胡亂劃了幾下,沒注意劃到哪裡了。」
鄢月勾唇:「你是不記得,還是……根本就不知道?」聲音,驟然轉冷。
月霄訝然:「舞兒,你的意思是,不是他做的?」
鄢月點頭。秦泰挑眉,眼眸含笑。
二姨娘雙眼一亮:「老爺,四小姐都說了,不是他,那、那更不會跟我有關係了。」
月霄不耐的看了二姨娘一眼:「若不是他,也不能認定,就與你無關。」
「我……」二姨娘咬了咬唇,又瞪向那人,「你說你,不是你做的,你承認個什麼勁?還拉上我?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是我做的,是我做的,四小姐,真是我做的!」那人似乎急了。
鄢月冷笑:「一般兇手被抓,首先就是極力否認吧。還有,既然我都說了不是你,可你看起來……怎麼一點都不驚喜,反而讓人感覺,很想擔下這筆罪呢?」
「我……證據確鑿,我否認不了。」
「是嗎?若說你不記得在我臉上劃了多少下,可你總該記得用什麼兇器劃的吧?」
那人詫異不已,脫口而出:「不是刀子嗎?」
話音一落,鄢月露出意味深長的笑,而月畫,袖下之手開始顫抖。
秦泰輕咳一聲,說:「不好意思啊,當初我救下月舞小姐時,她的傷口看起來,應該是被尖銳的石頭劃傷的,而不是刀子。」
此話一出,眾人反應各異。鄢月上前,一把揪着那人的衣領,冷喝:「說,是誰讓你來頂罪的!」
「我、我……」沒等那人說出口,只聽悶哼一聲,那人後背被一道有毒暗器擊中,當場吐血而亡。
鄢月猛地抬頭,只見一道倩影閃過。秦泰飛身躍出大廳,緊追而去。
鄢月臉色陰沉,看了眼月畫,目光落在那枚暗器上,拿出手絹將其收起。
「爹,看來府里怕是混進了刺客,您讓人好好查一查所有家僕,說不清來路的,一律趕出府。」
正好,藉機除掉監視她的人。至於那幾個混進來的天玄宮人,也可以趁機離開。否則,呆久了,恐怕會暴露身份。反正她已知是誰害的月舞,只要順着她那條線去查就可以了。
片刻後,秦泰回來了:「是新來的丫環綠桃,大姨娘院裡的。如今已服毒自盡。」
「沒問出什麼?」
秦泰搖頭,臉色嚴肅。鄢月沖月霄一點頭,拉着秦泰離去。
「定與月畫有關,荷清那邊可有消息過來?」
「嗯,當初買歌的,是一名年輕女子,但不是月大小姐或者她的侍女,那首歌,荷清賣了一千兩。」
鄢月挑眉:這個時空的一兩銀子,差不多相當於現代的400塊錢,一千兩也就是40萬。呵,還真是下血本了。
「一千兩,不是個小數目。大姨娘的娘家並不富庶,而府中掌管銀錢的為二姨娘,大姐自己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銀子。看來,果真有人在幫她。」
「那會是誰?那綠桃的功夫可不低。」
鄢月拿出那枚有毒暗器,若有所思:「大姐的價值,就是五皇子妃,莫非,是皇族中人?對了,荷清那邊有沒有查到這段時間大姐是否與可疑的人接觸過?」
「查到了,這也是我剛想說的,就是綠桃。」
鄢月眯了眯眼,將那暗器遞給秦泰:「你幫我帶給荷清,讓她去查一查這個。」
「哦。等會兒,我怎麼好像成了你跑腿兒的?」秦泰瞪着眼,似才反應過來。
鄢月勾唇一笑:「以後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儘管說。」
秦泰頓時眉開眼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