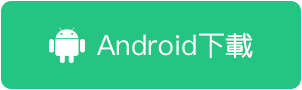深綠的葉片和紫色的花朵,在傍晚的微風中輕輕抖動着。
蔓藤間的男人穿着一身真絲襯衫,外套早不知道掉到那裡了,衣領一直解到小腹,敞開的衣服露出一大片結實的肌肉線條,性感的人魚線一直隱沒到西裝褲下。
女人身上如薄紗般的禮服也早就扯亂了,該遮的沒遮住,不該露的露一片,整個人又緊貼在靳烈風身上,手不規矩地在他的胸膛畫圈引誘,簡直是一副活色生香的春宮圖。
再加上那個女人有些蹭亂了的妝容,用腳趾頭想,也能知道着這一對男女剛才在蔓藤的遮掩下做什麼了。
靳烈風真是隨時隨地、和誰都能發情的種馬一頭!
阮小沫心底厭惡地想着,但心卻也止不住地收緊了。
她怎麼也沒想到,今晚真的會遇見靳烈風,還是在這種情況下。
男人深紫的眸子冰冷,目光落到了阮小沫身上,英俊的臉上面無表情,讓人猜不透他在想什麼。
「……你要我怎麼道歉?」阮小沫深呼吸幾口,出聲問道。
她不能再待在這裡,誰知道會生出什麼樣的變數。
可她今晚離開的計劃,不能失敗!
「道歉都要別人教麼?」女人倚在靳烈風懷裡,見阮小沫的態度比剛才軟化了不少,便得意地道:「好吧,那我就教教你,只要你跪在地上,用手把地上都收拾乾淨,我就不計較了!」
地上都是碎片,還夾在生鮮和碎冰中,徒手撿,妥妥地會被碎片弄傷,而且還要跪在地上……
這女人根本就是故意在為難她羞辱她!
阮小沫動也不動,只直直地盯着那個女人。
女人似乎被她盯得惱怒:「你看什麼看?!還不趕緊做!還想不想在帝宮做事了?!」
然後又立刻嬌滴滴地向男人抱怨:「靳少,您家一個下人都這麼欺負我,讓她道個歉都不願意,您要幫幫我呀~」
靳烈風隨意地站在那裡,任由女人像是沒骨頭一樣倚靠着他,深黑色的襯衫凌亂,領結鬆開歪掉,脖頸處有着煽情的口紅印,英俊的眉目間有着慵懶不羈。
放浪又誘惑的模樣,足夠讓身邊的女人,恨不得和他在蔓藤從里立刻糾纏一番。
女人面對他委委屈屈的模樣,和面對着阮小沫時的趾高氣揚完全是兩幅面孔。
但很多男人就吃這一套。
更何況靳烈風這樣的死色狼死變態。
自己本來就是靳烈風為了折磨才留在帝宮的,這種時候,他當然會縱容這個女人羞辱自己。
阮小沫明白自己今天是要被欺負定了。
「對啊……」男人性感磁性的嗓音懶洋洋地道:「跪下用手撿,是個不錯的主意。」
得到了支持,女人又往男人身上撒嬌一樣地蹭了蹭,一張艷麗的臉上浮現出幾分喜色,傲慢地對阮小沫呵斥道:「聽到了嗎?還不快做!」
阮小沫面色白了些,但背脊挺得直直的,說什麼也不肯跪下。
這根本不是她的錯,憑什麼她跪?憑什麼她該承受這樣的屈辱?!
她眼眶發熱,手緊緊捏成拳頭。
「你聾了還是傻了?讓你跪下用手收拾乾淨聽到了沒有——啊!」
女人尖酸呵斥的聲音隨着一聲慘叫,忽然戛然而止。
阮小沫抬頭,恰好看到女人正趴跪在那一片狼藉之上。
生鮮被突如其來的體重擠壓得粘膩噁心、還有碟子的碎片扎進她皮膚里,剎時血流如柱!
一道道鮮艷的血,從她的膝蓋上淌下,融進那片狼藉之中。
女人愣了愣,似乎是沒想到為什麼自己會被靳烈風推了一把,直接跌倒在這堆東西上面。
她眼角真切而迅速浸出了幾點淚光,轉頭看向靳烈風,楚楚可憐地喊:「靳少……為什麼?」
靳烈風垂眸地看着她,妖異的紫瞳里,沒有一點對她的留戀和同情,只有嫌棄和冷漠。
阮小沫也被眼前突如起來的這一幕弄懵了。
如果她沒有記錯,這個女人之前還跟靳烈風在蔓藤里做那種事情不是嗎?
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閉嘴!」靳烈風對她沒有半分的憐惜,語氣冷冽:「你說的,跪下用手收拾乾淨所有東西,有什麼問題?」
女人滯了滯,她那麼說,是針對面前這個不長眼的下人提出的,靳少怎麼會用到自己身上!
這一定是有誤會。
也許是靳少喝得有點多了,沒有聽清楚她的話。
女人試圖去抱靳烈風的大腿,溫順地向他解釋道:「靳少……我剛才說的是用在這個下賤的傭人身上的,剛才是她拿盤子撞了我……」
靳烈風抬了抬眼皮子:「她撞的你?」
女人以為他真是搞錯了,連忙點點頭,又矯揉造作地喊:「靳少……好疼啊……」
「是嗎?」靳烈風薄薄的唇角慢慢勾起一個弧度,深邃的紫眸微微眯起。
女人幾乎被他這個笑容迷得神魂顛倒,爬起來正要向他撒嬌,卻見他忽然收斂了笑容,渾身散發着森寒的氣息。
「你是聽不懂話嗎?」男人一字一字地從薄唇里吐出,薄情而殘忍:「我是讓你……跪、下、收、拾!」
阮小沫怔愣在那裡,差點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明明這個女人才和靳烈風發生了那種事,他怎麼會反而讓這個女人跪下去撿那些碎片……
女人的身子抖了一下,被男人身上的凌冽的氣場震懾。
她不敢再質問,轉過身,「咚」地一聲,直接跪倒在了阮小沫面前。
那雙做過指甲、保養良好的白皙的手,顫抖着伸向那堆碎片,伸手一抓,夾雜在碎冰中的細小的碎片,驀地刺進皮膚,柔嫩的皮膚上立刻就是一道血口子!
就在阮小沫覺得這怎麼可能的時候,男人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到了她面前,一把拽過她,才發現她手上本來即將癒合的傷口,被剛才那麼一蹭,又崩裂了。
阮小沫忐忑地想縮回手,卻被男人吩咐了人帶回房間消毒擦藥。
重新消毒上藥包紮,阮小沫在房間裡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團團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