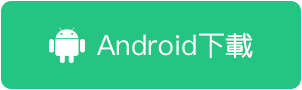這肯定是個懲罰了,不但是懲罰,簡直是虐待。
我承受了這輩子從未承受過的痛楚,等到席卿川從我的身體上爬起來之後,我的渾身像是被火車碾過一遍一樣。
他背對着我穿衣服,充分展示他完美的肌肉線條。
然而,我坐在沙發上,只能用靠墊擋住自己的胸部。
我的衣服已經被他撕壞了,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張牙咧嘴。
他走到柜子前拿出一件襯衫扔在我的身上。
我立刻穿上,慌手慌腳地系紐扣。
可是,我沒有褲子,我來的時候穿的是毛衣裙,從上到下就一件。
雖然席卿川的襯衣對我來說很大,但是也不能直接光着腿穿出去。
我勉強支撐着爬起來,渾身都在痛:「我沒褲子。」
他扭頭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滿嫌棄:「等會我讓宋秘書拿一條給你。」
「我跟她的尺寸不一樣,她的臀部比我大。」
「你觀察的挺仔細。」他扣好了扣子,系好了領帶,然後又套上了西裝外套,人五人六的,仿佛剛才那個野獸一般的男人不是他。
他站在穿衣鏡前整理自己的衣服,很用心地扣他的袖扣,他的袖扣很閃,在燈光下快要晃瞎了我的眼。
我莫名被凌辱,自然要問個清楚。
「所以說。」我蜷縮在沙發上,用大襯衫包住自己的腿:「我是個同妻?」
他好看的臉映在鏡子裡,看不出喜怒。
席卿川不是個面癱,除了面對我的時候,我有次看到他跟他的好兄弟聊天,笑的露出大白牙。
他不回答,我就當他是默認。
怪不得,我們結婚半年,他連眼皮都不夾我一下,感情他不喜歡女人。
可是,他今天為何這樣對我?
還是,他跟柏宇的好事被我打斷,他沒得發泄就發泄到我的身上?
我的身邊沒有同性戀的朋友,所以我還是蠻感興趣的。
「席卿川,像你們這種人,對女人也會有衝動麼?」
「我們哪種人?」他終於搭我的腔了。
他很臭美,一個領帶打了半天,都要系出花來了。
「我沒有歧視的意思,只是好奇。」
「你是說,我是同志?」他開恩瞟我一眼。
「不然呢?」
他忽然笑了:「怎麼觀察出來的?」
「柏宇都摸你的屁股了,還要我怎麼觀察?」
他向我走過來,兩隻手撐住沙發的椅背,居高臨下地看着我。
我不由自主地往沙發裡面縮了縮。
他的目光忽然停留在沙發的某一處,我追尋着他的目光。
沙發是米色布藝的,顏色很淺,上面有剛才被我弄髒的污漬。
我的臉紅了,聽到席卿川在說:「第一次?」
第一次很奇怪麼?
我的手緊攥着襯衣的衣角,悶頭不語。
這時,門被推開了,美艷女秘書的聲音:「席先生,您看這衣服可以麼?」
「放下。」席卿川說。
然後女秘書關門出去,一條連衣裙丟在我的身上。
粉橘色的針織面料,很裹身,我不喜歡這種衣服。
我捧着衣服小聲嘀咕:「不喜歡這個顏色。」
「你找我幹什麼?」他壓根不理我。
我這才想起我找他來的初衷:「奶奶住院了。」
「奶奶怎麼了?」他一秒鐘變臉:「你怎麼不早跟我說?」
「你給我機會說了麼?」我也來不及挑剔衣服的顏色和款式了,拿着就往身上套。
席卿川抓起桌上的手機就大步流星地往外走,我穿上裙子跌跌撞撞地跟着他。
出門就遇到柏宇,席卿川低聲跟他說着什麼,我趕緊離的很遠的站住。
席卿川說完了,扭頭看我離他好大一截,很不爽地高聲道:「我們身上有刺?」
何止是有刺,我曉得他們的秘密,還不遠遠地躲着?
柏宇回頭看着我,他的臉頓時又紅了。
他還真是一個愛臉紅的大男生,哎,我發現現在長的好看的小哥哥很多都是同志。
這讓天底下這麼多的單身女青年可怎麼活?
比如,讓天天都在談戀愛也天天都在失戀的喬薏大小姐情何以堪?
柏宇是席卿川的貼身助理,自然也跟着去醫院。
我們同一輛車,我很自覺地去坐副駕駛,柏宇和席卿川坐后座。
席卿川的車是商務,倆人對坐,我偷偷從後視鏡里瞄他們。
柏宇膚白貌美,就是典型的韓國花美男的那一趴,而席卿川的氣質就比較複雜了,他的長相既不算柔美也不算粗狂,應該可用精緻和雋逸來形容。
想當年,我和他訂婚前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在心裡驚呼,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好看的男人。
但是,結了婚之後我又驚呼,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難相處的人。
這麼看來,倆人居然配一臉。
花美男配俊男,怎麼看怎麼養眼。
忽然,我的座位被人狠狠踢一腳,不用說是席卿川。
他剛好踢到了我的屁股,幸好座椅質量好,不然的話我的屁股就要痛死了。
他發現了我在偷瞄他們,很是惱火。
他真小氣,我看兩眼又怎麼了?
我是撞破了他們的秘密,但是我也付出了代價啊。
我的第一次,居然交待給了辦公室的沙發。
到了醫院,席卿川匆匆忙忙地下車,把我和柏宇都丟在後面。
柏宇看到我,臉還是紅的,會臉紅的男孩子真的挺可愛的,我雖然慘為同妻,但是一點都不恨他。
反正我也不愛席卿川,席卿川也不愛我,我們倆的婚姻是怎麼回事我們心裡都清楚的很。
我和柏宇走在後面,席卿川走路很快,把我們扔的沒影兒了,我和柏宇同搭一部電梯,只有我們兩個。
我心中蓬勃的求知慾實在是按捺不住,便對側臉對着我的小哥哥開口:「柏特助。」
「您叫我柏宇好了。」他立刻說。
「哦哦,」我點着頭:「能問你一件事麼?」
「嗯,您說。」他好有禮貌。
「我想問,你和席卿川,哪個是攻哪個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