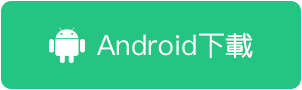凌晨的走廊上只剩下我、方越和曾純,我朝着他們走去,腦中回想起剛才方越沒有說完的那句話,還有他望着我,欲言又止的神情。
「簡寧,你聽我......」
啪!
響亮的巴掌聲在空蕩的走廊上格外刺耳,我冷眼看曾純心疼的摸着他的臉,質問我:「簡寧!你怎麼能打他?你是不是瘋了?」
「我是瘋了,但那也是被你們逼瘋的!」我沖他們低吼:「當初的事情不提,離婚就離的一乾二淨,但你們做的這是什麼事情?看不管我過的好,所以到我母親這裡找麻煩?」
「我母親當初是哪點對你不好?方越你告訴我,我母親有沒有對不起你,我有沒有?」
方越低頭不說話,他現在只要反駁一句,就會讓我看不起他,噁心他。
曾純擋在方越身前,振振有詞:「如果不是你母親說話過分,我怎麼可能會反駁?也不會造成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母親說了什麼話?」
「媽的事情真的很抱歉,今天在街上碰到她就說了離婚的事情,我以為媽已經知道一切就全部說了出來,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方越搶着解釋。
「她當街打罵方越,我肯定不能不管就上去反駁,她罵我狐狸精勾引你老公,我當然要說是你自己受不住男人,跟我什麼關係?」
曾純恬不知恥的說着事情的經過,我也從他們的口中知道了來龍去脈。
那時候離婚我擔心母親知道真相會傷心,所以寧願一個人承受也沒透露半分,卻不曾讓他們卻捅破。
耳邊是曾純喋喋不休的話,不停的重複着責任都在母親和我的身上,跟方越和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滾。」我輕聲吐出一個字。
曾純愣住,隨後大罵:「你算個什麼東西讓我滾?信不信我能讓你從公司立馬滾出公司?找個有錢的男人都忘記自己幾斤幾兩了,敢跟我叫囂!」
「這事情責任在我們身上,有什麼事你儘管開口。」
方越對我說完,轉身推着曾純離開,曾純不依不饒,一直說我們家是狗皮膏藥故意找茬,是沒錢的乞丐想利索他們。
我握緊拳頭,抬頭對他們冷笑:「你們家的一分一毫我都不稀罕,要是我母親真的有什麼事,你們就等着坐牢吧,我死都不會放過你們的!」
等他們離開,我來到監護室門口,坐在椅子上默默流淚,努力不發出任何聲音打擾到別人。
母親的危險期度過了,醫生說轉到普通病房看恢復情況好就可以出院,這是沒有時間限定的,因為要上班我還要請護工來照顧,那天方越交的錢早就用完了。
我又交的錢也快維持不住住院的基本開銷,我一個月四五千的工資根本就不夠,想到賣了房子解決困難,無奈房產證根本就不在我和母親的手上 ,沒有辦法變賣。
但今天,我突然想起一個人—傅鈞澤。
他說過不管我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聯繫他,他會幫助我的,他的話不斷浮現在我的腦海。
俗話說:人不能為錢被人戳脊梁骨。如果我因為錢去找他,只會讓傅鈞澤看不起我,甚至最開始的拒絕都會被認為是欲絕還迎,我到底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