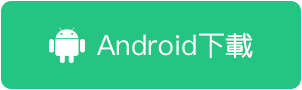而阮家……
阮小沫最擔心的,就是阮家的那些人,會把那晚的事添油加醋的告訴母親。
她緊緊蹙起眉頭,憂心忡忡。
她不知道,那些人會把多難聽的話傳到母親耳朵里……
阮小沫為難地咬住嘴唇,心頭一陣焦灼。
怎麼辦……
她……該怎麼辦?!
「哎!聽說了嗎聽說了嗎?」
「聽說什麼?」
「一周後啊,帝宮要舉行一次酒會,名義上啊是邀請各家和靳家有來往的家族參加,實際上啊……是給少爺物色在國內的聯姻對象的!」
走廊上,幾個傭人正聚在一起聊得火熱。
「都這麼閒有空討論主人的事嗎?!」
朱莉嚴厲的聲音,一下打斷了他們,幾個傭人立刻跟見了貓的耗子一樣慫了,不敢再多說一句。
阮小沫用抹布擦着樓梯上的雕花欄杆,默默地把剛才的話都聽進了耳里。
給靳烈風物色聯姻對象的酒會……
不用說,倒時候各色名媛淑女肯定紛至沓來,靳烈風絕對會被圍得無暇分身。
朱莉作為管家,注意力也肯定會放在宴會上。
只要她看好時機偷溜出去,找個比如公司出差的藉口,提前替母親過完生日,再趕緊回來,肯定不會被發現的!
這當中肯定會有風險,但只要她小心點,這會是她既能不引起母親的懷疑,又不會給阮家帶來麻煩的唯一機會,說什麼她都得試一試。
接連觀察了好幾天,阮小沫基本已經確定了到時候好偷溜的路線了,心也漸漸安定了下來。
只是她手上的傷似乎恢復得相當糟糕,雖然已經結了痂,她也已經相當小心了,但下等女傭的繁重事務,完全不可能給她時間養傷。
阮小沫蹙緊了眉頭,握着掃巴,在庭院裡掃着一個人根本不可能掃完的落葉。
掌心的刺痛一陣陣傳來,她知道傷口肯定又被磨破了。
可如果她停下來,其他仆傭肯定會給朱莉告狀,下次,就會是翻倍的責罰!
她只能一刻不停的做事。
「哎阮小沫!」
忽然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回頭,看到一個女傭牽着一隻金毛從庭院的小門走出來,不由分說地就把金毛的繩子塞進了她手裡。
「少爺朋友帶來的狗,你幫我看會兒!」女傭理所當然地道,順帶很快就離金毛遠了些。
要不是為了在少爺面前露臉,她何必那麼主動去牽這隻狗,天知道她最討厭狗了!
不過還好碰到阮小沫了,讓她替自己看着狗,等時間差不多,自己再過來把狗牽回去也沒人會知道的。
「可是我還要掃——」
阮小沫的話還沒說完,那女傭就跟沒聽到一樣,直接轉身走了。
低下頭,金毛抬着圓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她,大尾巴搖得正歡。
「看來沒辦法了……」阮小沫伸手摸了摸大金毛的腦袋,嘴角不禁露出一絲微笑:「那就陪你玩會兒吧。」
這隻大金毛可能是目前帝宮裡,唯一不會用鄙夷的目光看她的生物了。
附身拾起一根斷掉的樹杈,阮小沫一揮手,丟出老遠。
大金毛興奮地汪汪叫着追了上去,阮小沫趁機低頭掃落葉,等它撿回來,再丟出去。
不自覺地,連日來的糟糕的心情,似乎因為這一刻被拋到了天邊。
只是她沒發現,這一切都被樓上落地窗前的男人盡收眼底,原本就不佳的臉色,更是沉了下來。
這蠢女人的腦子裡到底裝的是什麼?
居然還有閒情逸緻和狗玩?!
深紫色的眼眸里,瞬間浮上一層怒意。
「烈風,你說我可怎麼……哎?烈風?烈風?!」
坐在會客室里鬱悶抱怨了一陣的年輕男人見他遲遲沒有回應,一抬頭,卻發現他面色不善地大步就朝門口走去了,茫然了一下,也立刻起身跟了過去。
「你還有心情和狗玩?!」
低沉的男聲里滿是不悅,似布滿烏雲的天空一般充滿了陰鬱和壓迫的感覺。
阮小沫被嚇了一跳,手中正要拋出去的樹枝一下掉在地上。
回頭一看,果然是那個萬年沒有好臉色的死男人。
「暫時幫別人看着,下等女傭不是沒有拒絕的權利麼?」想想她又沒有做錯什麼,收起見到他那一刻的驚慌,只淡淡地道。
金毛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以為她只是手滑,低頭叼起樹枝,不住地發出汪嗚汪嗚的聲音,還想繼續和她玩。
「閉嘴!」靳烈風聽得煩躁,冷聲訓斥道。
雖然是只動物,但金毛也本能地可以感受到一股危險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被凶,只好委屈巴巴地躲在阮小沫身後。
「咦咦?!怎麼了呀這是?」年輕男人也追了下來,還完全沒搞清楚狀況。
現在牽狗的女傭,雖然不是剛才主動來牽狗的那一個,但烈風怎麼會管下人工作這樣的小事?
靳烈風回頭,語氣沉沉:「把你的傻狗牽走!」
年輕男人渾身一激靈,下意識就把那隻和他一樣懵逼還委屈的大金毛牽過來了。
看氣氛不對,男人摸摸後腦勺,反應過來地大叫一聲:「啊!我突然想起我還有事,就先回去了!」
年輕男人帶着狗,臨走前,還朝阮小沫投去意味深長的一眼。
庭院裡,忽然就只剩下阮小沫和靳烈風兩人了。
阮小沫垂下眼帘,徑自繼續掃落葉,卻不料突然被男人抓住了手腕!
她皺着眉頭,抬頭看向比她高出許多的高大男人,卻聽到對方冷冷地道:「笑。」
阮小沫懵了一瞬間。
這男人……在說什麼?
見她沒有回應自己,靳烈風心頭又煩躁了不少,他抓緊了阮小沫纖細的手腕,霸道地命令道:「女人,沒聽到我說的話嗎?!」
剛才他從落地窗看的時候,她不還是笑得很開心嗎?
幹什麼在看到他的一瞬間,就擺出這幅樣子了?!
阮小沫:「……」
這男人是什麼時候腦子壞了?哪有突然就叫人笑的。
阮小沫當然沒笑,她也笑不出來。
換誰,突然被人莫名其妙地命令笑,也會笑不出來的。
她遲遲不肯按照他說的做,讓靳烈風心底的不快頓時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