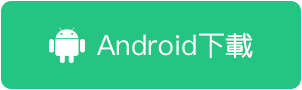距離那夜清醉,已有三日。
這日,和風煦煦,日頭正好。
莫阿九安靜立於府邸後院小亭中,靜靜望着風吹皺一池春水,不由得愣神。
方存墨明明已述職完畢,卻不知為何,今日異常忙碌,一大早便不見了蹤影,她卻也習慣了一人獨處。
「莫姑娘,門外有人求見。」管家恭敬上前。
莫阿九陡然回神,雙眸困惑。
她方才回京城,如今早已物是人非,知曉她身份之人唯恐對她避之不及,豈會有人主動前來尋找?
「我即刻前去。」輕應一聲,莫阿九起身跟在管家身後。
門外人,是一個身姿挺拔的男子,樣貌普通,卻明顯練家子。
甫一見莫阿九出來,那男子匆忙垂首不敢對視:「莫姑娘,這是主人給您的。」
莫阿九接過,是一封信。
拆將開來,熟悉的字跡。
「申時,聚賢酒莊。」
凌厲的筆鋒,偏生在尾部帶着一絲危險的綺麗。
莫阿九對這個字跡很熟悉,當初,便是這個字跡,在那個她分外珍視的錦囊中,留下了「留全屍」三字。
「我不去。」她信手將信扔與男子身上,便要離去。
「莫姑娘看看這個也不遲。」男子出聲攔住了她。
莫阿九微怔,側眸,男子手中,拿着一塊堇色琉璃。那是……小北的。
三年前,她被廢那日,身上首飾唯有一塊堇色琉璃,將其置於小北身側,惟願他這一生,無病無災,遠離朝堂,一生喜樂。
而今,竟已成為容陌威脅自己的手段而已。
「莫姑娘?」
「回稟你們主子,」莫阿九聲音平靜,「我會去的。」
會去的,卻再也不是因為那個男人了……
午後,將近申時。
莫阿九安靜坐於酒莊樓上雕花窗前,面前放着一盞茶壺,兩個茶杯。
她拿起一杯茶,濃郁的香氣,夾雜着說不出的苦澀,碧螺春的味道,她曾經厭極,而今,卻也歡喜了。
申時整,酒莊門口停下一輛青色轎攆,低調的奢華,一個男子下得轎攆,走入酒莊內。
那男子面無表情,卻掩蓋不住自身的華麗,多了一分邪魅的俊美,薄唇高鼻樑,就像是巧奪天工的工匠一點一點的雕刻出來一般。
莫阿九望着,呼吸一滯,手不經意緊攥杯盞,卻驀然鬆開。
很燙。
她再也不是那個被「燙」的遍體鱗傷也不知鬆手的固執女人了。
樓梯口一陣腳步聲,那抹身影終現身於二樓,其餘賓朋在男人上樓之際,竟均不約而同下得樓去。
看見角落中的女人,容陌雙眼微眯,竟有一瞬間,以為不過又是一場幻覺。
可最終,他不動聲色坐在她的對面,身姿雍容矜貴。
「用不用民女行跪拜之禮?」莫阿九抬眸,語調稀疏平常。
容陌瞳孔一緊,他還記得,這個女人曾說「我是你妻,怎可對夫君行君臣之禮」,可現在,她竟問他用不用跪拜!
「如果我說用,你會跪?」他語調嘲諷。
莫阿九依舊低眉順目:「會。」仿若天生無情緒般。
容陌的表情微緊:「那便跪吧!」他說得隨意。
莫阿九半絲猶豫都未曾,起身繞至桌外,俯身便要跪下。
「砰——」容陌手中茶杯驀然放在桌面,發出重重響聲。
而莫阿九,卻已跪在地上:「民女叩見聖上。」
容陌沒有應聲,他只是死死盯着跪在地上的女人,他看見她頭頂那一個孤零零的旋似乎在嘲諷他的自作聰明。
他以為她還是以往那個滿腹心機的皇家公主,而今……
民女,民女……她竟敢自稱民女!
「從古至今,朕還未曾見過宮內女眷逃至宮外之人,」容陌望着女人的頭頂,聲音逐漸冷了下來,「莫阿九,你倒是不曾介意給祖上蒙羞啊!」
莫阿九始終跪在原地,不曾言語半分。
可她的沉默,終究惹怒了容陌:「看來你也不在乎莫小北的生死了?」
「你想做什麼?」這一次,莫阿九終究無法鎮定。
「跟我回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