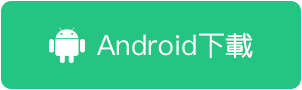……
「滴!滴!滴!」
「病人生命體徵平穩,輸血量四百CC,局部輕微擦傷,臟器運轉正常,無細小出血點。眼球部分缺失,視覺神經部分粘連,細小神經完全壞死,需要即刻摘除。」
「主任快下決定吧,若是不能及時摘除左眼視覺神經,將會導致神經連續性壞死,可能導致右眼連同失明。不能再等了。」
「立刻進行摘除手術,通知醫務科,進行器官移植準備。」
「可是主任,病人家屬沒到,並沒有簽訂器官移植手術。」
「聽我的,管不了那麼多了,他年紀還輕,若是因此導致瞎了一隻眼睛,對這孩子以後影響太大。協議稍後再補,你們立刻檢測,馬上進行器官移植,各項體徵進行檢測同步進行。」
「可是主任……」
「沒有可是,聽我的,院裡怪罪下來,我一力承擔。」
「主任……」
「手術!」
寧宇澤躺在冰冷的手術台上。
恍惚間,感覺到耳邊傳來一聲聲爭辯和無數個雜亂的腳步聲。
濃郁的消毒水氣味直直的竄進鼻腔,讓他的頭腦中混混沉沉的,似乎只有一雙大手在他的眼皮處翻來翻去。寧宇澤下意識的想要坐起身子,卻驚愣的發覺四肢沒有一點氣力,只能如同變成了一隻案板上待宰的光豬一般任人宰割。
我這是在醫院?
寧宇澤頭痛欲裂,感到有些恍惚。
他分明記得自己正在趕公司的路上,公司里那個四十多歲還沒嫁出去的老處女上司正在電話里喋喋不休的訓斥,寧宇澤不厭其煩,只是自己怎麼一下子就到了醫院?
對了,車禍。
寧宇澤想起來了,似乎有一輛失控的保時捷911呼嘯着朝他撞了過來,此刻,寧宇澤仍是能夠記起豪車中那張花容失色的姣好面容。是誰來着?似乎有些熟悉。
寧宇澤想着,睡意如潮水一般兇猛襲來,他只覺得眼前一黑便沉沉的睡了過去。
…………
「這是幾?嗯,那隻手看得見嗎?」
「嗯?有點模糊?沒關係,能夠感受到光感還能夠模糊的看見東西,這證明神經的連接完好。模糊只是暫時現象,隨着時間的推移只要不產生排斥現象,只會回復的更好。你就放心吧,大妹子,我當了一輩子醫生,絕對不可能用這個跟你開玩笑,我可以用我的醫德打賭,保證你兒子移植的眼睛跟之前一模一樣。」
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醫生一手拿着記錄本,一手捏着下巴,顯然對自己的醫療成果十分滿意。
「陳主任,這可是太謝謝您了。這可讓我如何是好,我聽說要不是當時您堅持力排眾議,要為我們家宇澤進行移植手術,恐怕他早就瞎了眼睛。他還這麼年輕,那該如何是好。謝謝,真是太感謝了。」聞聲,陳主任身前一個穿着寒酸的中年婦女頓時喜極而泣,她緊緊的攥着陳主任的手,頭入搗蒜連聲道謝。
說着就要跪地磕頭,陳主任苦笑了一聲,連忙將中年婦女扶起。
「大妹子,您這個大禮我陳某人可真受不起。」
「醫者父母心,我相信在那個關鍵的節骨眼上,任何一位用良心有醫德的醫生都絕對會做出如我一般正確的決定的。大妹子,你的心意我收下了,至於這下跪我老陳可真的承受不起啊。要是讓別人知道,還以為我陳某醫德有缺呢。」
「接下來就是恢復階段了,康復治療的藥物我已經開好,到時候你們只要去藥物室拿藥就可以了。」
陳主任笑道。
「康復治療?陳主任,這需要花多少錢,您知道我們家…………」
聽到陳主任開口,方才還歡天喜地的中年婦女臉上頓時愁雲滿面。
「大妹子,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畢竟牽扯到移植產生的排斥反應。」
「你們的家庭情況我也是了解過一些,我知道你家裡邊不富裕,所以我已經儘量將康復治療的藥物用咱們國產的代替,雖然進口的藥效更好,但其實相差不多。這樣醫保想必能報銷一部分,但就算是這樣,後續的康復費用恐怕也得需要五萬左右,你心裡可得有個數。」陳主任搖頭嘆道。
「五萬…………」
中年婦女嘴巴張了張,臉上的愁雲幾乎濃郁的都快要滴下雨來。
「媽,您別哭了,不行咱就不做康復治療了,我現在的情況挺好,能保住眼睛我已經知足了。」
寧宇澤看着眼淚吧差的母親陳雲芬,開口寬慰道。
「不治什麼不治,混小子,咱家還輪不到你來當家作主。媽說的算,要是你真有個三長兩短,哪天媽死了怎麼能有臉去見你們寧家的列祖列宗?你爹死的早,留下我們孤兒寡母的相依為命。媽好不容易把你拉扯這麼大,怎麼能看着你這麼年輕就瞎了一隻眼睛?你放心,就是花再多的錢,媽也能掙。」陳雲芬瞪着寧宇澤,咬牙道。
「可是咱家…………」
寧宇澤舔了舔嘴唇,苦澀道。
可誰知,他話還沒說完,就被陳雲芬打斷。
「沒有可是,兒子,你就聽媽這一次,你這眼睛咱們一定要好好治。你還沒娶媳婦,媽還指望着你給媽生個大胖孫子呢,要是因此瞎了一隻眼可怎麼好?兒子,錢的問題你不用操心,媽還沒老到動彈不得的地步,媽再借一借,這世上沒有過不去的坎。媽不和你多說了,得回去給丫頭做飯了。」
說完,陳雲芬硬邦邦的留下這一句,顫顫巍巍的就出了病房。
聞聲,寧宇澤母親陳雲芬倔強的背影,他嘴唇蠕動,開口欲言,可終究沒多說什麼話來。
陳雲芬其實年紀不大,今年還不到五十歲。
只是母親顫巍巍遠去的那佝僂的脊背卻如同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糟老婆子。那背影落在寧宇澤的眼中,卻一下子就讓他通紅了眼眶,豆大的淚珠子滴落在病床潔白的床單上。
寧宇澤心中泛起無比的苦楚和酸澀來。
母親陳雲芬說的無比輕鬆。
可寧宇澤又不是年少無知的小孩,他怎麼不知道自家的情況?為了他移植的手術費用母親幾乎跑遍了所有能張嘴的朋友,現如今,就連自家的親戚都避之不及,母親又能從哪裡能借到分毫?
陳雲芬要強了一輩子,含辛茹苦將他們兄妹帶大,付出了不知多少。
五萬,五萬塊錢。
興許對於那些高高在上的有錢人恐怕只是一頓飯錢,一個包錢,僅此而已。
但對於一個隨時都處在支離破碎邊緣的單親家庭來說,無疑是壓彎了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它壓彎了母親日漸蒼老的脊樑,它壓白了母親耳邊的鬢髮,讓他們這些底層苦苦掙扎的小民只能眼睜睜的接受現實的殘酷和沉重。
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吶。
我不想母親被金錢壓彎了腰,不想讓母親為了區區五萬塊錢就在親人朋友的奚落中低下頭顱。
我更不想就這麼懦弱平凡的活一輩子。
我要變得強大,我要讓母親,讓妹妹安樂一生。
我…………
不甘心。
……